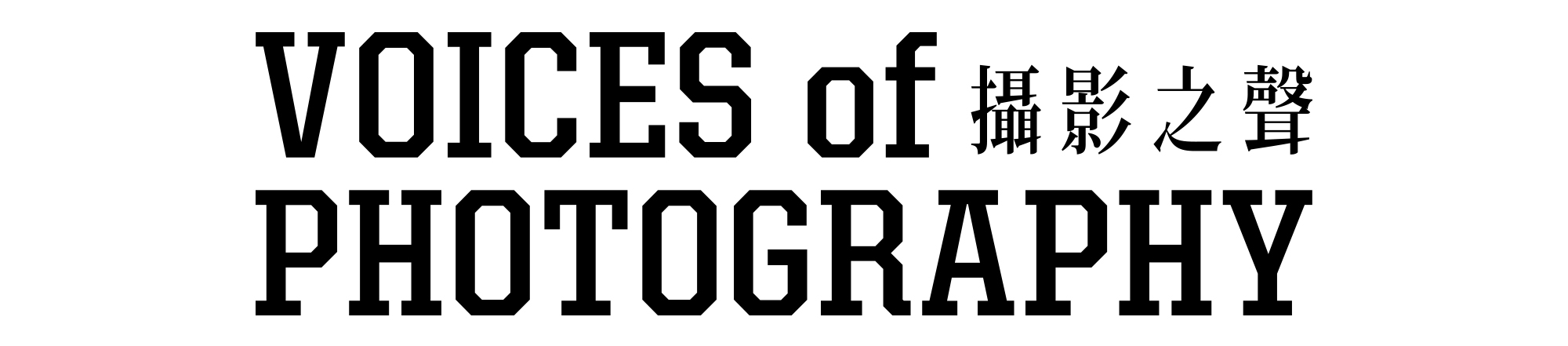文──張世倫
如果說家父有什麼優點,其中一項或許就是很會「留東西」。
「留東西」這個習慣,雖然多年來給家人帶來一些難以避免的困擾(並且也傳染給他的孩子們),但他的書房與儲藏室,卻也時常成為重要且獨一無二的檔案庫。
前陣子整理東西時,找到一張具有意義的物件,是家父的至交好友黃永松先生以他為模特兒、繪製於1964年4月14日的一張蠟筆肖像。
今天正好也是4月14日,因此這是一張剛滿「六十年」歷史的友誼見證肖像,令人百感交集。
當時的年輕文青迷戀James Dean那種「無來由的叛逆」(Rebel Without a Cause),將其轉化並移植為存在主義的移情對象,並在穿著髮型與喫煙姿態上百般模仿,家父也不例外。
他常說自己沒有繪畫天份,羨慕高中時便結識訂交的好友黃永松在這方面的長才,而兩人在六〇年代的青澀時期,也各自用相機與畫筆、將彼此當作免費的模特兒,留下了一些對現代藝術進行想像的初期創作。
不過這張蠟筆畫,還有一些其它故事。
在父親的檔案文件裡,另留有一張黃永松發表於1980年《中國時報》的短文,講述自己求學時代經歷的諸多挫折,以及如何在失敗中更加堅定了友誼與信念的重要。
這張繪製於1964年的蠟筆畫,背景是聯考失利多次的黃永松當年在家父鼓勵下,決定聽從本心、投考在板橋浮洲里的藝專,為了準備術科、勤於練習,因此以他為模特兒進行的繪畫習作。
而且,「這樣我們這些朋友又可以常見面了」。
短文裡漫不經心提到的許多細節,其實都與後來傳世的重要作品有些關聯,例如五指山的禪寺與生定法師,即為家父以黃永松裸背為主體的〈新竹五指山〉(1962),以及陳耀圻《上山》(1966)的歷史脈絡。
不過文中最令我讀到觸動的,是黃永松文中提到的八斗子海邊段落。
父親幾年前因為健康欠妥,無法親自前往在瑞芳「好好基地」舉辦的「幽暗微光」礦工攝影展,因此委託黃永松代為出席開幕式。
當天活動結束後,黃先生交付給我一件在附近廟宇求來的保平安品,然後漫不經心地說,「年輕時我準備重考,換過很多地方住,有陣子的流浪處就在八斗子附近,你父親會騎摩托車來這探望我,兩人一起看海,也去過這間廟⋯⋯海還在,廟也還在。」
在4月14日結束前,張貼這幅六十年歷史的畫,並轉貼這篇文章的節錄如下,紀念父親與黃永松先生的這段友誼。
他們現在應該也在一起上山、一同看海了,自由自在。
寫於2024年4月14日
以下節錄自
黃永松,〈寫給聯考落榜的朋友〉
原載於《中國時報》第八版,1980年7月29日
二十多年前,當我還在龍潭國小讀書的時候,一直是個「標準」的好學生──意思是說我的學科成績都還不錯。畢業的時候,全校有三位同學考進建中(初中部),我還是其中之一。但是顯然地,這種微小的成就和榮譽卻為我帶來重大的壓力,我只是個十二歲的孩子,考上了聯考,卻彷彿要肩承起這一生中所有的理想、和理想之前的煎熬。
上台北唸初中,我寄居在一位親戚家裡,這個家庭中的每個孩子都很優秀,考得好初中、好高中、好大學⋯⋯這些「別人的事實」也圍砌成我的不快樂。註冊的第二天一早,我被叫起床,讀那科從來不曾接觸過的英文,我還能清楚地記得:那時不過清晨五點鐘光景。
於是我的初中生涯展開了,至今回顧起來,幾乎乏善可陳,我大約只能擁有兩個印象:一個是下課時分,整個大操場中到處「布滿」了玩啊跳啊的同學,在那塊塵土飛揚的地上走過,隨時會有遭到球擊的危險。另一個,我經常塗塗畫畫,參加了西畫社,並且總喜歡到植物園裡去寫生、或者只是坐坐、逛逛。──如是三年。
三年後我再度參加聯考,唸上了成功中學。依照家人的意願,唸的是甲組。高中時代,我有較多的能力與時間選擇自己所需要和喜愛的事物:參加柔道社,當上了社長,還率隊出征,摔出了全省比賽的亞軍。我更交上一位與我切磋無間、影響至深的好朋友:張照堂。我們有相同的興趣和關注:繪畫、攝影、文學、和現代藝術,當時的物質條件很差,一本畫冊已經是相當優厚難為的精品了,同學們爭相傳閱,翫讀再三,我的興致更大,還時常用功「創作」一些作品。這些作品真的沒人會欣賞,只有和張照堂交換著觀賞:彼此作觀眾、作知音,發出指正和喝采,我們居然如此的作過癮的自由創作,這些使我的高中歲月豐盈起來。

然而初中生最現實的問題畢竟還是來臨了。民國五十一年(1962)夏天,我又投入了升學聯考的戰場,這一次規模更大,戰況更烈,戰績卻奇慘──我落榜了。這個打擊對我來說還不如對家人來的重大,他們很難想像:一個鄉裡優秀的小學生,出門遊學六年,却帶回來如此深沉的失望。這一年當中,我被管束的相當嚴格,上補習班,在外租房子,埋頭於幾何三角的無味糾葛之中。──回想起來,這是很危險的一種挑戰,挫折加上厭倦,我却竟然沒有「變壞」,没有「出軌」。也許這要從我所熱中的一切說起。
那一年張照堂保送台大土木系,對他的興趣說來,土木工程是不足以言理想與志願的。他仍舊寫詩、攝影;我也没有間斷自己的繪畫習作,更時常充當他照相機前的模特兒。我們交了許多為現代藝術作開發、推廣努力的朋友。「現代詩」詩刊的創辦人紀弦是成功中學的老師,「東方畫會」、「五月畫會」也亦師亦友地啟發了我們許多新穎獨特的藝術觀念,我們好像是在遊玩;但是認真而嚴肅,並且深信其中有永恆可待的理想。
現實的另一面是:第二年我再度名落孫山。
家人已經對我的學習前途感到徹底的無望了,父親知道我喜歡畫畫兒,問我:有没有意思到美術工藝社去當學徒?學畫廣告看板,有一技之長在身,也不愁將來遊手好閒。
這一年,我擁有了較多的自由,仍然常和張照堂一塊兒,又攝影、又作畫,自不免天南地北,滔滔雄辯,他已經是堂堂正正的大學生,我也還理直氣壯地堅持著自己想要學習、感受的一切。
我認定了這樣的消磨是有價值的。
早先柔道隊的同學們雖然也落了榜,後來又都考進海洋學院,他們重新組織起柔道隊,找我去擔任臨時的教練工作,我就在八斗子的海邊住了一陣子。碧浪藍天,鮮貝危石,構圖著我優游閑散的日子。
後來我該是倦遊返鄉了罷?村居的日子没有維持太久,家裡來了位父親的老朋友:生定法師。他聽說我屢敗屢戰的「苦業」,大約是體會到我即使在家,也無法安心唸書,便說:「這樣吧,跟我到寺裡住一段日子,山中清閒,讀書自在。」
於是,就像傳統的中國士子,明山秀水之間,寺鐘伴讀,燃香薰書,卻真是不勝其清美了。我於是來到竹東五指山的觀音禪寺,老禪師永遠也不會逼我讀教科本,他總是布衫芒鞋、雨傘包袱,紅塵裡出出入入地實踐著他的信念和哲學。寺裡還住著一些修行的人,他們每天清晨起來練拳習武,我也跟著捉摸揣摹,練會了兩套拳法,和一些內家的吐納功夫。──在無言與無形中,這點啓發對我應該是重要的潛移默化。雖然當時我仍舊不能忘懷:現代藝術在塵世裡的喧騰和掙扎;雖然大自然的佳景與籟音也正時刻召喚著我個人的藝事好夢,然而直到第三次聯考,我一直待在山上,讀各種書籍:我想讀的,以及不想讀的。偶爾,張照堂會來寺裡盤桓一陣,告訴我大都會裡藝文發展的風雲人事,那真是值得關心,值得憧憬的盛況;但是我也一次一次地發現:現代藝術也在這個偏遠的山坳裡展現身姿:山川煙靄,就是我心神耳目的美學教室。張照堂也同意這一點,有一回他寄給我一個厚厚的包裹,打開一看,是一冊五月畫會的畫冊。就是這樣了,我想:友情如寄,投遞著我慮接神馳的未來。
第三年,我又要考大學了,一樣濃烈逼人的夏天,從山中帶來的清涼顯然不敷應用了。最逼人的是:我一直對自己下決定:不再考甲組了,不要再被「分發」志願了。我必須自己選擇──讀美術。
張照堂的家住板橋,附近有一所國立藝專。「你來考藝專吧,這樣我們這些朋友又可以常見面了。」於是我臨時決定改考乙組,而且有術科。只填了三個志願:師大、藝專和文化學院三個美術系。──和其他人填得密密麻麻的報名表格相較,我內心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奇妙感覺,也許有點得意,得意於我堅守一個信念和抱負,那是我的「志願」!
應考是如此艱難,我没有學過炭筆素描;水彩畫也僅憑著高中以前平日練習的基礎;國畫方面,只有臨時和張照堂上街買了本芥子園畫譜惡補──三項術科,無一足道,但是多少年來我所關心、熱愛的道途畢竟在我自己的抉擇下舖展開來,我必須全力奔赴。
應考的過程仍舊匆匆,這只是奔赴新前程的一個起步,我愉快地揮畫著首次使用的炭筆──我選擇了它,然後,我終於上榜了。
當我坐在國立藝專的教室裡,眼中簡陋的桌椅窗門卻盈溢起無限的光潔。遠遠的牆垣之外,是那條古老的鐵道,小火車嗚嗚嘟嘟地列隊行過,行過它自己的那條軌道⋯⋯
⋯⋯這些足跡敷疊著我的青春,更舖構起我生命中一些不可動搖的價值:友情和理想。

圖 | 張照堂家屬提供
發佈日期 | 2024年6月14日